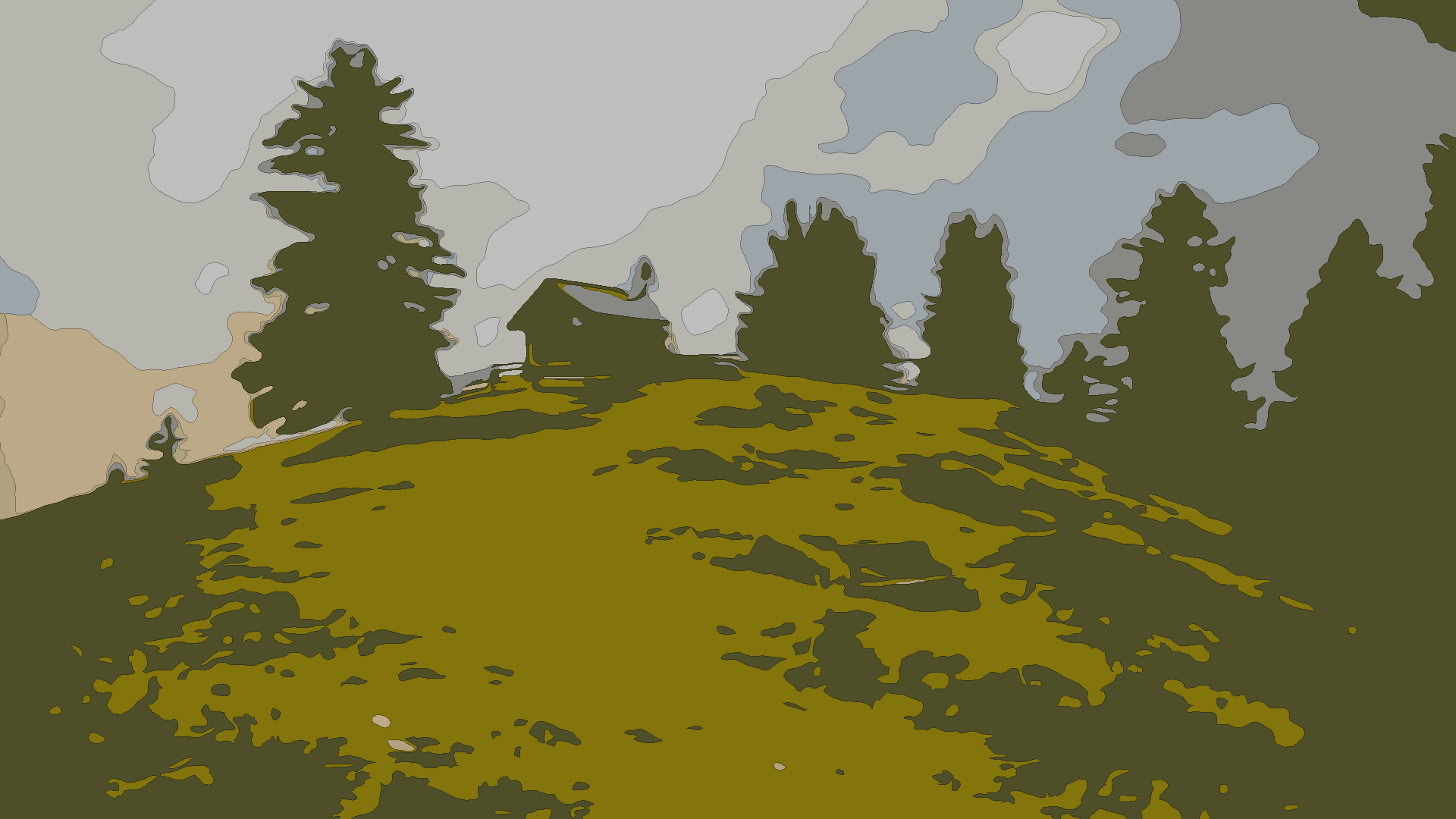孤立的围楼中,鲜有人在空地上闲逛,但一到课间,栏杆便成片地长满了人。他们在蠕动、在伸展,享受着短暂的休憩。过不了不久,先是沉重的“︁咚”︁,再是熟悉的音阶,将教室变成人口密度最高的“︁地区”︁。
教室是静寂的,可当生物学老师告知一模提前到学期末时,全班都炸锅了。[1]
在这样的压力之下,我却以不合规的姿态来到社团招新现场。一般的高中生只有两次机会在招新现场,一次在成为新生之后,另一次在下一届新生入驻之后。在高二之末,旧一届的社长卸任,新一届的社长上任。但出于某种原因,我要到十二月初才会卸任,临时又彻底地划分剪切线。显然,高三的学生没有,也不应该有社团课,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,我的任务却有两个。
我意识到这一点时已是倒数第二节下课,那时舞台已经升腾,不过只是根据时间推算得来。于是我跑到班主任那询问是否能去招新。他听了我的言辞,有些惊奇,指尖划过课表,停到下午最后一节课——自习。“︁我看看是什么课……英语。”︁他转过头来,又想了一小会,说:“︁好吧。”︁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我立刻跑回教室,提起帆布袋准备出发。
那两位熟人正站在外面走廊边的平台聊天,却注意到提着帆布袋的我,过来问我“︁你怎么就去了”︁。我将事实一一道出,他们露出羡慕的姿态,眼神有些发亮,又夹杂着一丝遗憾。
“︁我想看学妹的表演。”︁“︁可惜我以部长的身份去不了。”︁这样的话语接连不断,但我必须出发了,时间来不及了。我挥手告别。
如果说围楼是关外的话,那么学校大厅就是市中心。我要从楼梯口下来,穿过一条小径,越过一条主干道进入小围楼,又走过漫长的走廊,不过还没到就传来嘈杂的人声和活泼的音乐声混合成的……杂音?它告诉我不应该来这里。
终于云拨见日,天花板也瞬间抬高了几层楼。我在陌生的人群中找到了社团的摊位,就在左手边,三位高二社员正在上工,还有一位高三现任社员客串,但他时限已至,短暂慰问后只能遗憾离场。我跳上高台,舞台上五位少女在做什么?几场表演后,棍社的人上来了,我放眼望去,直到表演结束,都没看到一个熟人,想必也已经彻底回归现实了吧,是否还有微光一样的重现呢?
不对,我不是过来招新的吗?怎么还当成借口来逃避呢?不过,谁不想抓机会喘口气呢?任由他人牵引,任由作业缠身,任由小测闪击,这是人类期望的结果,不过人类并不是我们。
啊,我确实是来招新的。我被台上莫名其妙的说唱劝退了,也许是我无法理解,也许是普通话过于字正腔圆了。总之,回到这里,形形色色的人群依次流动,大部分看都不看一眼,有少数人停留下来,却指着那两个字,觉得太难而散去,只有少数中的少数,要么被说服,要么默默地走到展板旁报名。模糊不清的说唱仍在轰炸我的耳朵,但紧接着就是街舞社的主场,不过与我又有何干?我理解不能。
我实在待不住了,于是打算逛逛。中午没人的时候已转过一圈了,结论就是,庆幸没让广告公司来设计海报,否则我社又沦为刻板印象的产物之一了。我喜欢摄影,不过限于在虚拟世界中随意截图;喜欢文学,却难以抽出时间写些灌水文章;喜欢音乐,但与众人几乎没有交集。我从人群的缝隙中流过,却看到一个从未见过的社团——日摇社,摊主看起来应该是社长,热情地递给我一张海报和一份……纸片人?我抬头扫了一眼展板,又低头看了一下海报——说是日摇,怎么全是少女呢?疑惑之余,我流回我的摊位,偶然在人群外看到一位日语老师拿着日摇社的海报离去。已经写满了一张报名表,又有零零散散的新生被展板吸引而来,我也不时跟他们聊上天,诉说那段黑暗的历史,皆引于一人之心、一人之行的悲剧。
又是说唱。我看了一眼时间,对于高一、高二来说快下课了,可对高三来说差得远呢。过了几分钟,大厅也没多少人,于是大家一起收了摊,留一支笔、一张表,各自去吃饭。从楼群走出,我望向围楼,那边像是时间静止一样。我找了个座位吃晚饭,过了一会,偶然发现同班同学坐在旁边的桌子吃饭,看来他们从“︁时停”︁中解脱出来了。我们互相打了招呼,随后又像陌生人一样各吃各的。
晚自习前五分钟到班,桌上又多了一套试卷——真好,这正是我进度落后的证明,那么,他们的进度就不落后了吗?我猛地想起,当我在周中躺了两天回来,发现桌上的试卷并非简单堆叠,却建成了幻象方尖碑注视着我。突然,那“︁方尖碑”︁的尖顶变成透明的红,另一边的眼神想要传达什么,我不清楚。
有人问我社团招新开不开心,我只能回答:目的不纯。不管是报名的人也罢,还是我,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条道路——逃避。不过即使从南跑到北,从东跑到西,现实仍然充满真实,理想仍然充满幻想。既然如此,不如不要逃避、不要幻想好了。
最后并没有,还是像上一届那样放在第二学期初。 ↩︎